第九章 大年三十
呼啸的寒风停止了浅吟低吼,空气变得混浊起来。天边浮动着厚重而低垂的乌云;大朵大朵的雪花像是刚从棉桃里摘出来的湿棉絮,沉重而迅速地降落下来。山、树、河床、马路和房屋几乎就在瞬间全都变白了。四周万籁俱寂,只听见雪片坠地的沙沙声。几十分钟后,黑河坝便被一床雪白松软的大毛毯覆盖起来。
吃罢晚饭,我们一家人围在火炉边赏雪闲话。来黑河坝十年了,还是第一次见下这么大的雪。浓密的雪花漫天飞舞,低矮的天空看着毛蓬蓬的,屋里被雪光照得光亮而且舒适。罗广放寒假了。读了半年大学,他个子长高了,肌肉长结实了;以前红扑扑的圆脸变成了轮廓分明的方脸。人变得更加稳重,性情安静而沉默。我在汉中航空基地的一家工具厂工作,因离家近,基本上每两星期回来一次。再过两天就是除夕;自从我考学出去后,全家也只有春节才能团聚。
今年春节对我们家有特殊的意义。我参加工作了,罗广又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已彻底断了后顾之忧。喜上加喜的是父亲、母亲的户口已和留守处其他家庭一道迁到合肥去了。
几个月前,合肥16所领导换届。新所长姓杨,是个蔼然长者;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留守处四十多家的户口全部迁到了合肥。几天前,杨所长携人事处沈处长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到陕南山沟的留守处,访疾问苦。许诺尽早在合肥盖房,把大伙接过去,实现全所大团圆。
母亲听了,喜之不胜。可一转念,他们去了合肥,不就把文新丢在陕西了吗?烦恼了两日,猛可地记起所里有个政策,凡本所职工,身边无子女者,均可调一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孩子入所。现在广儿在读大学,他们身边厥如,符合这一政策。母亲立马撺掇父亲,两人一起找到杨所长,要求调大儿子回所。杨所长说,这事归人事处管,你们先去找老沈;等他向我汇报之后,再作决断。母亲、父亲马不停蹄地找到沈处长,说明情况。沈处长答应得挺干脆,可以调,不过得等你儿子见习期满了以后。再有,你们想清楚,调了大儿子,小儿子就不能回所了。父亲尚有些犹豫,母亲却一锤定音,小儿子先不管他,我们就调大儿子。
母亲看着罗广,歉疚地说:“哥哥的事迫在眉睫,我们只好先救他了。广儿,你不怪妈吧?”罗广恬静地说:“应该先调哥哥。我毕业还早呢,况且也不一定想回所。”我故作谦让道:“调不调我无所谓,我可以考研究生考到合肥去。”父亲恶声喝骂:“你他妈就只会吹牛!在学校里连个本科都升不上,还考研究生呐!”罗广颇以为然地说:“哥哥考研,恐怕基础太差。”母亲说:“所以我才要调哥哥嘛。他这人惫懒得很,又没个定力。把他一个人丢在这边,我怎么放得心下?”
哥俩去走廊上厕所。外面雪小多了,撒纸片似的稀稀拉拉地飘着。苍紫的暮色中白皑皑的山峰仿佛静静燃烧着的洁白的火焰。积雪冷嗖嗖的寒气扑面而来,给人一种凉爽而愉快的感觉。
进屋父亲又在和母亲吵嘴。母亲的弟弟王泽平不久前来了封信,说他们村有个人在地里挖出了一坛银元。那人穷疯了,正往外卖钱;价格很低,十几块钱一枚。问我们家要不要。母亲格外动心。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她久有置些金银首饰留给子孙后代之意。她和父亲商量,寄一千块钱回去,让泽平买几十块银元送来。父亲坚决不同意,粗声大嗓地嚷道:“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八成是你那个宝贝弟弟赌钱赌输了,设计骗你一点钱花花。”母亲双眉一竖:“放屁!泽平根本不是那种人。”
“哎呀呀!”父亲失惊打怪地叫道。“你当他是什么好人?不务正业,贪赌成性。家里穷得瓢泼汤稀。又不想着如何挣钱,就知道向两个姐姐伸手!”
母亲连称放屁。丈夫如此诋毁弟弟,她心里十分恼火,也尖酸刻薄地贬低起罗家人来了。父亲自然不依,把王泽平骂得体无完肤。夫妻俩唇枪舌箭,吵个没完。
老舅王泽平一辈子也没交个好运。退伍回来不肯安心务农,先是跟人合伙养蜂,一年未尽,蜂已跑光。后来又贩金银首饰和银元去广州卖,头一趟赚了千把块钱,又全部买了货;再次去广州交易时,被警察当场捉住,血本无归。此后霉运就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干什么亏什么。雪上加霜的是搬进山区的那一年,老婆被疯狗咬了一口,找了个乡下庸医来看,不知怎么就把人治死了;丢下一儿一女。女儿妹子才一岁多,儿子尚在襁褓。老舅一贫如洗,养不活两个孩子,就把儿子送了人;自己带着妹子和老母回中河口种了两亩薄田,聊以糊口。后径小姐夫撮合,他又讨了一个眇了右目不会生育的女人。本来小日子也还过得,可他偏又染上了打牌的恶习;十赌九输,家里常常吃了上顿缺下顿,饿得妹子皮包骨头,嘴尖颧耸,跟只瘦猫似的。
在万福庵的时候,老舅常去借钱。搬到黑河坝后山隔水阻,只来信借过两次;和从前一样,有借无还。86年夏天,父亲和我回了一趟老家,见他住一间像是要倒的破茅屋,家徒四壁,穷得伤心,便留给他两百块钱。87年秋天,外婆病危,母亲为钱的事和父亲吵了一恶架,然后将家中的存折一古脑揣在身上,扬言要和父亲离婚,一径回了湖南。外婆见到母亲,病竟一天天好了。母亲在老家呆了二十多天,到底牵挂陕西的亲人,尤其是在略阳读书的罗广,就给老舅留了笔钱,取道西安回了黑河坝。母亲负气走后,父亲以为她真的不会回来了,一种孤独的恐惧感攫住了他,他觉得整个世界空荡荡的。在写给我的信中,父亲的语气悲惨凄凉,再三表达了要和两个儿子共度余生的决心。母亲来西安时,我和她谈到了父亲的这种心态。母亲好气又好笑,说:“要离在没有你们两弟兄时就离了,何必等到现在?他这人死小器,外婆病危我多带几百块钱都不行,我不得好好吓吓他!”父亲见到母亲回来,这一喜非同小可,满面堆笑地把她迎进家门,再也不提钱多钱少的话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和母亲言归于好了,却始终改不了他那爱吵爱骂的脾气,而且知道母亲不会弃他而去,更加有恃无恐;和母亲一语不合,便大吼大叫地发作起来。我和罗广好容易劝他俩停止了舌战。母亲便征求我们的意见:“文新、广儿,这银元将来是要留给你们的。你们说是买还是不买?”罗广笑笑,不置可否。我却极力怂恿道:“买,当然买。这种‘袁大头’在南方一块能卖五十,现在只要十几块钱,是乡下人不懂行情。我们不买就太可惜了。”父亲瞪眼骂道:“你他妈胡说八道!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母亲得到我的支持,便决意要买了。她鄙夷地看着父亲说:“没见过你这么小器的人,一花钱就跟割你的肉似的。这银元我买定了;不花你一分钱,你反对也没用。”
自从母亲开裁缝店起,家里的财政就分开了,母亲挣的钱归她自己支配,父亲管不着;父亲的工资奖金也由他自己攒着,不和母亲照面。我和罗广读大学的费用、家里的柴米油盐等日常开支全部从母亲的钱里支出,父亲不时还从母亲那拿点钱买烟抽。
父亲知道母亲决定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转,就叹气道:“你要寄就少寄点,也算是减少损失吧。”他心里老有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预感。母亲被他说得有点怕了,第二天就只寄了六百块钱。
年三十那天,积雪未消。苍天之下座座雪峰宛如朵朵美丽洁白的花朵,屹立在无风的天空中,宁静得像是这永恒的时空。
母亲在厨房烧年饭,父亲帮忙打下手。我和罗广清闲无事,缩在房里听音乐。罗广上大学之初,母亲便寄钱给他买了一台录音机,供他学外语用。罗广便买了几盒流行歌曲磁带,以饱耳福。我们家这么多年连收音机也没买过,哥俩从小就与丝竹无缘,乍一接触,顿感新鲜美妙。
《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剪梅》等影视歌曲婉转缠绵,荡气回肠;《猛士》迪斯科磬磬轰轰、疯狂嘈杂,烘染出一种温馨喜悦的节日气氛。惜哉父母不知欣赏,只说是噪声,吵死人了。
下午四点,年饭做好了,荤素满桌。母亲烧菜,讲究数字吉利,非九则八;最多的一年烧了十六个菜。开饭前父亲点燃一挂鞭炮,噼噼啪啪放完;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火药香。一家四口于是落座,彼此招呼着动了筷子。
父亲指着桌上的鸡鸭鱼肉,如沐春风地说:“这桌菜在饭店里起码也要三、四百。我们花了多少?一百出头。两百多块钱的赚头就是我们老俩口一天的辛苦劳动啊。”母亲笑道:“你出了多少力?打杂而已。哪一样菜不是老娘亲手烧出来的?”
父亲今天心情特别好,也不和母亲吵,继续喜眉笑目地说:“我们家这几年多亏有一个会挣钱的裁缝,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天天有肉,年年有鱼。就是神仙也不过如此。”
父亲年年这个时候都要发些类似的感慨,并提起他小时候过的苦日子:为筹学费挑水卖,一担水卖伍分钱;上学只有一床棉被,垫一半盖一半等等,颇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
我和罗广却无法体会父亲的心情,只顾吃菜。母亲有两道菜烧得特别可口:红烧排骨和冰糖肘子。前者香酥脆嫩,绵不粘齿;后者甜腻糜烂,落口消融。每年最见底的就是这两个菜。
吃完年饭,父母摆开阵势,开始包饺子。年初一吃饺子是北方人的习惯,我们家到黑河坝后才沿袭了这一习俗。包饺子得仰仗父亲;母亲不会擀饺皮。父亲擀得一手好饺皮,这手艺还是他在部队学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擀,一个包,边干活边话旧。这是他俩一年到头最亲近、最融洽的一天,彼此没有怨气,相互不再争吵,轻松写意地享受着这份和乐与恬适。
包好饺子,母亲又开始洗一家人的衣服。元月初,我们家以两千九百多元的高价买了一台被倒爷倒得十分紧俏的十八吋“黄河”彩电。看了十来天就坏了。为了不影响看春节晚会,母亲数日前亲去勉县将它修好了。晚会开始时母亲还在走廊里晾衣服。母亲每年年三十都是从早忙到黑,从未准时看过晚会。而且每当新年钟声敲响之时,她便会下厨房为大家做宵夜,通常是醪糟鸡蛋。
正月初几的一天,冰消雪融,阳光清丽。母亲带着我们两弟兄信步登上楼后的那座山冈。极目远眺,整个黑河坝尽收眼底。山还是那么青,水还是那么明,只是从前的那种喧嚣扰攘已不复存在。寂寥的山村里,饮烟袅袅,鸡鸣狗吠,黑河沉思般悠悠流过;土厚民淳、风恬俗美的黑河坝一如这亘古绵长的青山,将世世代代长存下去。母亲喟然长叹:“我们再一走,这里就更冷清了。我们家来黑河坝十年了,对这儿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可要走的终归要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妈这十年来,没一天闲过,为的是把你们两弟兄拉扯大。现在文新自食其力了,广儿还有几年。等到了合肥,广儿大学毕业了,妈就可以啥都不干,彻底休息喽!”
兄弟俩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和皱纹清晰的脸庞,心里唯愿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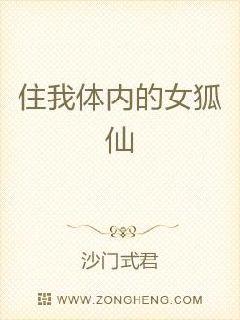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