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 抚流民巧收众英豪
本回诗曰:
男儿处世有端方,身未显时名已扬。
不求四海同感德,但教天道得昭彰!
话说蓝衣仙子被那怪一吓,惊得一声娇呼,竟而跌下界来,高欢大急之下连忙坠下云头去寻。岂料偏在这紧要关头,猛又听数声咚咚急响,立时一惊而醒,原来却是一梦。
高欢见有人拍门甚急,立即将锦帕收好,起身开门。门甫一打开,却见高岳母子持着灯笼满头大汗,一脸惶急。未待高欢开言,高岳急忙提了桶水冲入屋内左右环顾,像在寻找着什么,待见一切如常,又不禁挠头抓腮,满脸诧异。
高岳老母更是惊疑不定,直盯着高欢瞅了半晌,才喃喃道:“奇哉怪哉!却才老身入厕,见此间红光四射,还疑夜半火起,极是耽心贤侄安危,忙唤岳儿提水来救。今见贤侄无恙,实乃万幸!只不明方才红光从何而来,贤侄可知?”此时高岳也在一旁大点其头,极口称是。
高欢听到红光四射数语,暗忖定系那锦帕缘故,只是当下却并不愿说破。于是惟淡淡一笑,指着那兀自闪着星星微光的油灯道:“阿婶、洪略过虑了,想是贺六浑晚间吃得醉了,一时不觉入梦,竟忘却吹灭这盏油灯罢。”
高岳闻听此言,直将一颗大头摇晃不止,连连道:“油灯微末之光,断不致如此,况且这是小弟进屋方才点着的呢,绝计不是。”高欢未置可否,止说夜已深沉,阿婶、洪略早些歇息为是。高岳老母闻言又盯了高欢半晌,蓦地眉头一舒好似若有所悟,旋即点了点头这才拉过高岳出门而去。
高欢不禁心中偷乐,当下忙闩了门,重卧榻上。只是却不好再将锦帕就着灯火观看,于是便吹灭油灯,和衣而眠。继而寻思梦中情形,那蓝衣仙子品貌非凡,岂非正是绮夜。一念至此,顿觉胸怀大慰,少不得又掏出锦帕覆至面上,循着缕缕幽香兴冲冲觅那旖旎芳梦去了。
次日晨起,高岳老母不知哪来的劲头,非但早已备好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席间更不迭劝食,殷勤异常。高欢揣度多半系昨夜缘故,便即一笑而过坦然相受。餐毕自要临别,高岳母子却仍欲挽留,连那小小少年高归彦也是依依不舍。高欢暗叹一声,不由分说留下半袋阿堵物,道一声珍重,便单人独骑重奔返程。
又行得两日,不觉已至平城近郊,步入一条山林小道。高欢看看天色渐晚,正欲快马加鞭早些寻一打尖借宿之处,不料此时偏听得左侧林间突起喧哗,甚且还伴有打斗声响。莫非是行路人遇上山野强贼不成,那可真真危乎险哉。
想到此,高欢连忙策马奔了进去。可待入内一瞧,却哪里是什么强贼。只见得一群男男女女或坐或卧,散布在树丛间,个个破衣烂衫犹带血迹,面黄肌瘦几近枯槁,尤令人触目惊心者,是众人那沮丧无助的眼神中甚且透着显而易见的绝望……唯远处有七、八人扭作一团,似在争抢着甚么。
高欢大感不忍,遂连忙上前喝止。那扭打的几人蓦见来者威风凛凛,身着官家服饰,略作犹豫还是停了下来。高欢立又抱拳朗声道:“诸位父老请了,在下怀朔贺六浑,不知诸位因何致此,又为何事所忧?”众人闻听他寥寥数语,雄壮之中不无关切,顿时齐齐看了过来。此一照面间,忽听有人语带兴奋地呼道:“高队主,是我等平日时常念叨的高队主来了,尔等还不快快上前拜见!”
众人闻听此言,竟似饮了太上老君的还魂丹,立时一抖精神,翻身而起,迅速聚拢了来。高欢略感诧异,又听那唤己作高队主的汉子忙不迭自报家门,原来却是平城执役时柔玄镇佣丁,曾私下来过高欢营队,因权宜计不得已才又离去。但经那平城之旅,对高欢其人可谓一见难忘、敬服有加,返归乡里后更是不忘时常大为宣扬。是以今番境况相见,自是格外欣喜,也格外恭敬。况众人中不少早已风闻高欢德才,夙怀无限景仰。于是至此皆陆续下拜,口颂:“小人等见过高队主”。
高欢一时又是感动又是怜悯,忙唤众人起来说话。
众人遂才你一言我一语,道出了个中原委。敢情大伙儿多半来自距怀朔不远的柔玄、怀荒二镇,前些日柔然(又称蠕蠕)骑兵南下劫掠,朝廷官军抵御不力,数百村落非但财物俱被洗劫一空,大量百姓更是被掳为奴隶,供那蠕蠕兵随心所欲胡乱驱使。其间休说挨打受骂乃家常便饭,甚且稍不合那天杀贼子贼意便有残手断足之虞。众人实在不堪忍受那百般凌辱,便觅得一贼子夜宿酒醉之机,偷偷逃出。但一路饥羸交并,终不免死伤过半。又因家园已毁,屋舍已残,不得已求助各大镇军衙门,以期得一安身之所、立命之资。
岂料他等竟似商定好一般,概不接纳,只说甚么此间粮饷匮乏,尔等宜往平城受抚云云。众人皆是寻常百姓,哪里识得这等官腔,于是便又心急火燎赶往平城。可谁曾想一双双赤脚历经千辛万苦好容易抵达,却只见故都执守远远已将城门紧闭。尤为可恶者,彼等非但不纳,待众人行至近处,见皆无意离去居然污为蠕蠕奸细,不由分说便用乱箭一阵射杀。众人惊惧之下没奈何只好暂保目前性命,躲至这山间树林捕些鸟兽苟且度日。
高欢听至此,心中恻然、愤懑之情早已密密交织,当下不由得恨声道:“贺六浑此番自洛都而来,所见亦是骇人听闻。朝廷如今这般上行下效,实令天下子民心寒!”
众人听得此言,更是咬牙切齿,有人甚且愤愤骂道:“如此朝廷,要他何用!”
高欢闻言暗叹一声,又慨然道:“列位父老万勿忧切,若蒙见信,请随贺六浑同归怀朔暂居何如?”
此语一出,立时群情大振。短暂沉寂片刻之后,猛听有人大呼一声:“高队主救苦救难,我等誓死追随高队主!”众人听得微微愣了一愣,迅又醒过神来,连忙齐齐随他高呼起来。一时间欢声雷动、愈聚愈大,那“誓死追随高队主”七个字真可谓声震林野,气荡山谷,久久不能平息。
高欢瞧着眼前情形,也是大出所料。当下心海一阵翻腾,目中竟不免有些儿湿润,却不知是悲是喜,是惊是叹……
过得好一歇,待高欢抱拳拱了拱手,群情才渐趋缓和。此刻再展眼瞧时,却见众人无一不是一改愁容,喜形于色。继而更纷纷拍掉昔日落魄尘,掸去旧岁倒霉灰,意气风发地跟着眼前这丰神朗朗的青年男子踏上了新的征程。
其后只因人数太多,委实无恁大客栈,是以便一路披星戴月,兼程前行。高欢早已将马让于老弱妇孺轮流骑乘,而众人感动之余更是振奋无比,个个心中均憋着一劲儿,直远远赛过当年越墙窃香抑或花烛洞房。
如此仅过七日,便已抵怀朔。高欢先将众人安顿于白道之南自家老宅附近,且留下随身全部银钱,再嘱托邻里乡旧全力接济,但容己回衙稍作部署,立时便来再作安排。众邻里自高欢幼时便屡受恩惠,多半早有思报之心,加之眼下情形估摸着定又非白供吃喝,自然一口应承。
暂行别过众人,高欢即飞马赶往镇军衙门交了公函,又略略与一众同僚寒暄几句。只是四顾之下却不见孙腾,稍稍一问,才知数日前老户曹外出之际跌落山崖一命呜呼,而在这地广人稀之塞北边疆,此户曹(掌管征丁纳税等)一职断不可与关内都会相提并论,实乃大大苦差。偏那杨均已命孙腾入替,此刻犹征税未归。高欢闻听此讯,心中不禁一阵窃喜,忖道:“真乃天助我也!”于是当下也不多闲话,只暗邀昔日旧部入夜过府一叙,言讫便匆匆打马归家。
一别月余,姐弟夫妇、兄妹子侄乍见之下,亲昵欢喜自不待言。
高欢少不得一一抚慰,继而才略诉洛中见闻,其间巧遇冯绮夜一事当然省去不提。待叙至征西府横祸、众流民惨状,乃姐姐夫听得俱是一脸愤愤,娘子娄昭君也忍不住喟然太息。高欢瞧瞧火候已至,于是顿得一顿,正色又道:“由此观之,天下不久必生大乱,我辈亦断无独安之理!今番贺六浑意欲倾其家财,勉尽安抚之责,不知三位至亲可赞同否?”说罢更以满含期待的目光瞧着三人。
娄昭君果非等闲女子,闻听此语不但不恼,且对着夫君凤目深注、字字坚定地道:“夫君高瞻远瞩,万世难及!妾身由衷欣慰,断无不从之理!”
尉景本还犹豫,听弟妹尚如此慷慨,又见高芸拿肘来碰,忙也言道:“欢弟深谋远虑,人所共知,姐夫亦断无不从之理。”
高芸只待他话音一落,立也嘻嘻一笑,半是戏谑半是认真地道:“我家欢弟自幼行事远近叹服,阿姐岂有不从之理?”
高欢见他三人语调相访,俱是这般支持信赖,感慨之余更是欣慰难言!当下遂展颜一笑,朗声道:“贺六浑有亲若此,真乃人生第一快事!”此时此刻,虽是即将散去家财,他几人心中却是无比振奋、格外激越。
晚膳时分,孙腾等人如约来访,高欢当即拉他等一道用膳,他几人虽不再直属高欢统领,但每每见着高欢,仍是无比恭敬,一如前时。
不多时吃喝已毕,高欢即携了他几人连同尉景一齐去往白道之南老宅附近。孙腾等恰也知情识趣,一路并不多问。待见得众流民,高欢方将此事大体诉及,并着他等寻些人手、觅些空地,协助修房建屋,所需银两则自家一力承担,临了又瞩令严加保密,且设法免去众人户册名头。孙腾等向来心下所服唯有高欢,况知此番事关重大,自然不敢怠慢。如斯安排妥当,已近寅时光景,他几人这才各自归家分头安歇。
此后月余,高欢日日亲去检视,见到大众居有所安,身有所养,自是欣喜异常。而此时大众对这位令己安身立命的大恩人早已敬若神明,每每相见,往往涕泪交并,动辄便要五体投地。高欢也必次次亲去扶起,温言相慰。
这一日高欢方一归家,立闻中庭笑语阵阵,极为欢欣融洽。入内一瞧,原来却是段荣夫妇和娄昭到了。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儿,眉眼很是清俊。只独不见娄文君,略略问及,才知是月前已然出嫁,丈夫唤着窦泰,字世宁,大安人士。只因彼时事起仓促,是以不及来怀朔相邀。
高欢一向旷达不拘俗礼,自是毫不介意。当下一把抱起那小孩儿,轻轻一刮他尖尖鼻头,柔声道:“好个惹人怜的小娃娃,汝叫作甚么名儿哩?”他这一不留神,竟不自觉地带了点冯绮夜的江南口音。
众人听得俱是一愣,却见那小孩儿眨着扑闪闪的一双迷离眼,定定瞧着高欢,忽地偷抿小嘴一笑,稚声稚气道:“姨丈不记得铁伐了么?铁伐可记得姨丈哩!”听这语气,竟是依样学样现炒现卖。
众人皆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起来。高欢其实早猜到这小孩儿是段荣之子段韶,铁伐正是他的小字。只是当年自己仅在成婚之际见过一面,那时他还不满两岁,方在呀呀学语。不想这小家伙记忆如此之好,竟能记得。
高欢遂大笑着亲了小段韶一口,直夸道:“韶儿如此明敏解人,姨丈如何舍得忘却哩!”众人绝少听高欢这般说话,一时笑得更为酣畅淋漓。个中久别重逢情绪,自然喜不胜言。
已而酒足饭饱、夜阑席散,段荣方道出平城秩序混乱,此番前来正是欲在怀朔安家,也好时常与高欢一处,凡事有个计议。
高欢自然大喜,于是次日便亲往自家不远处寻了一处宅子,只待洒扫干净,段荣夫妇便搬了过去。娄昭则在两位姐夫处随意走动,倒也乐得自在洒脱。自此两户你来我往,互通有无,亲密得了不得。
算来匆匆数月又过,堪堪岁已末,偏偏寒未尽。上元之夜,娄昭君临盆产下一白胖儿男,但见他额宇含英,眉目凝秀,颇似乃父当年形状。高欢无限欣喜,因思自家平生之志,便替爱子取名为澄,暗喻澄清天下之意。段荣听得此名也连声称妙,言语之间全是夸赞。一大家子因这新添娇儿,日日皆是喜乐无边。
如此转瞬到得百日,高欢又主持大摆筵席,款亲待友。甚么经高欢安抚的二镇流民、怀朔的新故邻里、镇军衙门的旧友同僚、连平城蔡俊也被娄昭寻来,众人皆齐齐相贺,轮番祝祷。一时真真热闹无比,欢洽非凡。
不过就中也有几个生面孔,却是不请自来。一位年约三十五六,清瘦儒雅,乃是新任怀朔省事,自称贱姓司马名子如;另一位年过而立,体态肥大,系那司马子如老友,唤着贾显智;还有一位与高欢年纪相仿,生得目光炯炯,白面有须,姓刘名贵,乃是秀容行商,常年往来六镇贩马。他三人皆是异口同声道:“在下等久慕高函使德才,早欲登门拜会,止恨夙无机缘。今藉小公子百日,幸得如愿!”
高欢见他几人谈吐不俗,料必也有些儿本领,于是当下忙也客套几句,引入己座畅饮叙谈。
席间他三人眼见大众对着高欢统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俱不由得暗暗讶异。
这一番宴饮欢聚,直折腾得三日三夜方散。众人尽兴之余,对高欢的钦敬仰慕愈发深了一层。
待过得两日,孙腾又同司马子如三人联翩来见。那刘贵肩上还架着一只白鹰,说是“新近觅得,悍捷迅猛异于常物,小子不敢独享,特邀高函使一道射猎”云云。
高欢许久未尝弦上滋味,此际睹物思逞,不免技痒心动,自然立时应允。可巧两位姐夫左右无事,蔡俊也尚未离去。于是索性携了娄昭与他三人一同前往。
却说九人九骑出得街衢,正拟纵马北向。忽听有人远远呼道:“敢请高公留步。”众人循声转头去瞧,却瞥得一身形短小的缁衣汉子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黄马,正奋力招手,遥遥而来。待行至近处,渐才瞧清此人尊容。只见他额头凸起,几乎前倾过半;两腮凹陷,偏又后撤太甚;唯那目光却是如鹰似隼,隐隐透着一股凶顽之气。
众人看得不禁暗暗皱眉,高欢却玉面如常,只顺手一勒马缰,抱拳道:“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又怎生识得某贺六浑呢?”众人见高欢发问,便皆停了下来。
那缁衣汉子闻言裂嘴一笑,忙拱手回礼道:“高公大名如雷贯耳,六镇百姓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小的姓侯,人唤狗子,前几日还到府上吃过小公子的百日酒呢!”说罢仍裂着大嘴,嘿嘿痴笑不止。
高欢闻听此言,这才模糊忆起前番宾客之中似乎确曾有人与此君面目仿佛,此等古怪形容世间断不会多,想必是他无二。于是当下微微一笑,颔首道:“原来是侯兄。”
那侯狗子听得高欢如此相呼,面上立时极不自然地道:“高公切莫取笑小的了,小的自打娘胎出来尚从未有人这般相称,听着甚是不惯。高公直管唤小的狗子便是。”
众人听得这话皆有些儿忍俊不禁,高欢却是不动声色。只听那狗子自个也讪讪一笑,顿得一顿又道:“高公与诸位敢是同去射猎罢?还盼能一道捎上小的呢!”众人闻言未置可否,皆齐齐望向高欢。
高欢见此人虽则形貌鄙陋却似乎极有心计,况瞧他模样又这等迫切,拒而伤之实为不智,于是略一沉吟便点头一笑道:“此间又非华林苑(彼时皇家园林),飞禽走兽能者得之。汝既有此意,又有何不可!”那候狗子听得此言顿时大喜,连忙打拱谢过。于是当下便跟在九人之末,飞驰向北。
已而但见一路风激尘扬,人欢马跃,角弓漫舞,衣带乱飞,那白鹰傲然盘旋之际,更不时凌空厉啸几声,仿佛在向四围禽兽示威一般。奈何其时虽已仲春,偏生北地草芽初萌,百兽尚匿,是以奔了许久,却并未觅得半个猎物的影子。
众人正在感叹“健儿空负手中器,何处去觅用武乡”,突见前方草丛晃动,一只褐红色的野兔似箭脱弦,飞蹿而出。
众人大喜,急忙策马去追。那野兔受此惊吓,更是愈蹿愈快。众人因先前白白奔了半日,心中无不憋闷得紧,故而此刻皆有心拿这倒霉畜生寻些乐趣,一时倒并不急于张弓搭箭。直到头顶那白鹰似是忍无可忍,几番厉啸不止、作势欲扑,刘贵拗它不过,这才撮嘴打个胡哨,唤它去逐。那白鹰得了此令,立时怪啸一声,伸出利爪疾冲直下,瞅准那畜生褐红头顶便是闪电一击。众人看得心潮澎湃,正欲拍掌叫好,谁知那野兔却也厉害,堪堪于大祸临头之际就地一滚,竟而瞬间没了踪影。
众人见状大惊,忙围拢过来,只见地上草叶间覆着一拳头大小的洞穴,那野兔想是由此遁去了。
众人大悔之余多半懊怅不已,唯高欢眼波一转,忽道:“常言道‘狡兔三窟’,吾料这畜生惊惶之下必从别处逃逸,我等还宜速往四下觅而追之!”
众人一听这话,顿觉有理,忙又四散开来分头去寻。果然止过片刻,即听娄昭在西侧数十步开外高声叫道:“孽畜在此,哪里走!”说着即飞马追了上去。众人听得精神大振,忙也拍马跟上。
可这次那野兔却是当真狡滑得紧,偌大空旷之地不挑却偏专拣草丰土薄之处逃匿,如是三拐两拐,每每仗着长草作屏总能躲过白鹰凌厉的攻击。那白鹰几番扑空之后直激得它怪啸连连,似乎在怒声咒骂不擒此贼绝不罢休!
说来还真个是“有志者事竟成”,过不多时,便见前方草尽泽现,却是一片茫茫水域。那野兔眼见是无路可逃,微一翘首张望,即被那白鹰一个俯冲,逮个正着。
众人大喜,忙疾驰而至,准备下马活捉。岂料就在此刻,蓦见黄影闪动,汪汪连声,那白鹰、红兔俱被一物飞快压住,拿了个结实。众人定睛看时,却不知从哪里冒出一条大黄犬,口中衔了鹰与兔,正欲拔腿而走。
众人又惊又怒,纷纷喝骂。高欢并不多言,止用手往身后一探,立时引弓满怀,一箭飞出,正中那黄犬颈部。那黄犬受此重创,猛地甩出嘴中鹰兔,惨吠几声,狂奔几步便即狗头一歪,倒地毙命。众人忙去检视地上鹰兔,却也早已呜呼哀哉。
正没个理会处,却忽见水泽西畔两个黑衣汉子急奔而至,一瞥见地上黄犬翻眼蹬腿之状,顿即失声悲嚎起来。众人方欲开言,不料他二人忽又飞快欺身上前,一把扯住高欢衣襟下摆,嘶着嗓子道:“汝还吾阿黄命来!”余众见高欢竟被他二人抓扯,统皆大怒,齐齐喝道:“尔等休得无礼!”说着立时便要动手。
高欢连忙摆手制止,正拟措辞开解,突又听一声怒斥破空而来:“阿大、阿二两个混账东西,平白瞎了狗眼,竟胆敢触犯至尊么?”一语未落,已是人随声至,却是一位双目黯黯、白发苍苍的老婆子。她虽则拄着长拐,偏偏脚下如飞,进退自如,待到得近前,立又奋杖去击那两黑衣汉子,且口中兀自骂道:“汝这两个畜生,还不松手。”那被斥为“混账”加“畜生”的阿大、阿二见势不妙,连忙脱手闪过一旁。
众人见此情形,皆是惊疑不定,就连高欢也略感错愕。却见那婆子驱罢阿大阿二,立又冲高欢抱杖一礼,满含歉意地道:“犬子乡野村夫,愚陋不识天颜。老身管教无方,竟致冒犯,还乞至尊恕罪!”
众人听得此言,更是万分惊异,呆若木鸡。方才“至尊”二字还疑自个听错,这回“不识天颜”等语,却是入耳分明。因此等辞令称呼乃是臣民对九五之尊的皇帝陛下专用,而瞧这老婆子眼下语气神情,简直与参见天子并无二致。
高欢毕竟是高欢,果然与众不同,在稍露讶态后便醒过神来,微微一笑道:“老人家说笑了,贺六浑亦乡野粗人,如何敢当。只是方才情急之下失手折了令郎爱犬,此刻犹不自安呢!”
不曾想那婆子闻言摇首不迭,愈发正色道:“老身岂敢妄言,至尊不必过谦,更毋需自责。区区一犬值得甚么,况得殒至尊之手,倒应算那畜生命厚呢!至尊若不嫌弃,请暂移驾舍下小坐片刻如何?”
高欢听得这番诚挚之言,一时也无暇细想,又兼眼前之人神秘莫测,实欲一探究竟,于是便欣然道:“岂敢,如此贺六浑等恭敬不如从命。”语毕,便唤众人同往。
众人犹自惊愕万状,猛地闻听高欢召唤,当下也顾不得许多,唯有一齐跟着那母子三人同往泽西而去。
约摸百余步后,泽中出现一条宽仅三尺许的土石小径,恰容一人一骑鱼贯而行。好容易到得尽头,却见前方修竹竿竿,密密匝匝、郁郁葱葱,隐然有俊挺苍翠之致。已而进入竹林绕得几绕,又见一处茅屋掩映其间,门廊檐角若藏若现。
高欢随时留意,此刻见这竹林茅屋互为映衬,犹似暗合奇门生克之理,心中不禁更觉讶叹。谁曾想这百丈草泽深处,尚别有如此福地洞天!
思忖间,已然到得茅屋跟前。那婆子忙拣竹凳招呼众人坐下,又唤两儿温酒造饭,杀鹿待客。且言:“山野之地别无长物,可巧前日犬子捕得野鹿数只,今番正好派上用场。”众人闻言一喜,方欲客套一番,不意高欢却笑道:“看来我等今日甚有口福呢!”
那婆子也自笑道:“至尊他日富有四海,又岂止区区口福呢!”
高欢本淡淡笑着,但听这神秘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称己为至尊,却也不禁心中一动,于是旋即便敛容正色,徐徐道:“老人家怎生称呼?可否有劳再瞧瞧贺六浑众位亲友呢?”
那婆子闻言忙道:“至尊有命,安敢不从!实不相瞒,老身夫家俗姓谢,略通扪声之术(古代术数,以声论贵贱祸福,今已失传)。如此还乞贵友循次发声一二,待老身为至尊逐一听来。”说着便即起身从众人面前一一经过。众人也俱依言各自及时道上一两句问候。
这一圈走来,但见她频频点头,不住发笑,只于贾显智同那候狗子面前时笑容稍稍凝住。临了又转回高欢跟前,含笑道:“恭贺至尊,诸公俱不失为至尊麾下一班好文武呢!”说至此顿了一顿又指着候、贾二人道:“只是可叹此二位晚景欠佳,未免略显美中不足。”高欢听罢,当即微微一笑,颔首谢过。又念及这婆子夫家姓氏,原是江南名门大族,只南朝刘宋以后,支脉渐散,颇为凋零。莫非彼与伊人一般皆是江南人氏不成?
遐思至此,蓦见众人俱有些儿手足无措,显见是受了方才婆子之言影响。于是忙又岔开话题顽笑几句,众心这才稍安。
过不多时,酒肉迭出,馨香四溢,那婆子忙引高欢等上桌,众人因奔了大半日颗粒无收,此时早已饥肠辘辘,故而当下稍作谦让,便皆各展所长大嚼开来。只最肥美处,却又不约而同让与高欢。
这一餐直吃得个个腹撑胃胀,方才作罢。因见天色不早,高欢便向婆子一家告辞。那老婆子兴许觉着委实宾主谊深,仍是坚持领着两儿送出竹林,又亲眼瞧着众人先后过了草泽,才回转而去。
众人又奔了盏茶工夫,个个俱不免心事重重。尉景实在忍耐不住,忽道:“方才之遇闻所未闻,着实神奇无比。许是仙人指点也未可知呢!”孙腾、娄昭闻言连忙附和。
高欢瞥见众人面上仍是恍如置身梦幻,不禁暗忖:“却才那婆子虽则神秘,却应是深谙奇门遁甲、五行术数之世外高人。但若仅是如此,她那一番奇言众人未必深信。不如略施小计,稍加促成。子茂兄即便勘破,亦必不负我。”心下计较已定,于是便皱眉道:“奇人术士自古有之,神仙之说,究未可知。既如此我等何不再往一探,或可解去心中疑窦呢?”
果然段荣一听这话,当即心领神会,连忙接口道:“此言甚是,吾意也是如此。”众人稍稍一思,无不大觉有理。于是又齐齐调转马头,再行折返。
待至草泽西畔,一行直奔了数百上千步,却再也找不到那隆起泽中的三尺小径,遥望前方,只见水波茫茫,漫无边际。又哪里有甚么竹林茅屋!众人大惊,连高欢自己也觉大出所料。本道此番再来,所见必然有些儿变化,谁曾想这变化竟是如此之巨。
众人又觅得许多时候,仍是毫无所得。尉景早已忍耐不住,喃喃道:“尔等何必再劳心费神!看来今日定系仙人指点无疑了!”
说话间孙腾、娄昭、段荣猛地和他互望一眼,立时翻身下马,一齐向高欢下拜,口中颂道:“属下参见主公,今后主公但有差遣,属下等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蔡俊、刘贵、司马子如、贾显智见状也不甘落后,赶紧同拜道:“属下见过主公,虽则仆等才薄德寡,如蒙主公不弃,今生亦愿誓死追随,绝无半分二心!”
只那候狗子似乎因腿脚不甚利索,动作稍显迟缓,饶是如此,这等关键时刻,他又岂肯怠慢,只见他慌忙间奋力一跷短腿,扑通一声跌在地上,口中高声叫道:“主公在上,狗子参见来迟,还乞主公恕罪!”
高欢见此情形,心中大喜,只面上仍不露半点声色,当下忙一一扶起,慨然道:“贺六浑得众位相助,夫复何憾夫复何求!”言讫又抚慰了一番,约定平日里仍以旧称相呼,免露形迹,唯私下可另当别论。
众人一时俱慷慨激昂,诺诺连声。那候狗子方才因先天不足,稍落人后,似乎一直心有不甘,此时忽见他嘿嘿痴笑一声,猛地上前半步,两腿一错,立又拜了下去,且一脸恳切地道:“狗子遇上主公好似重生一般,恳请主公另赐一名,恩同再造!”
众人见他此状听他此言,一时差点喷饭,但碍于新主公在侧,只好生生忍住。
高欢微微莞尔,暗道:“此子先天虽则不足,后天却实有余。这等狡狯油滑远非常人所能及。不过大丈夫处世还应海纳百川,量才取用。况且此情此景,倒也有趣。”一念及此,于是当下便眼波一转,徐徐道:“千古风流逐征尘,人移物换景常新。汝‘狗子’之名过于鄙俗,既是如此,今后便唤着侯景罢!”
众人闻听此言,立时连声称妙,那方得新名的候景果真有如获了重生再造一般,霎时间乐不可吱,手舞足蹈拜谢不迭。
高欢凝神再瞧向那茫茫草泽,眼波中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渐渐荡漾开来。
经此一番际遇,众人相待高欢自又大不相同,返归之时,高欢居中一马当先,众人随扈分列左右,颇有从此君臣携手,横行天下之慨。
自此以后,他几人往来高欢家中更是密切,或谈各地见闻;或论南北局势;又或飞鹰走狗、往来驰骋,日子倒也分外洒脱。
如是三载弹指又过,其间高欢另去得洛都数次,公务之暇,便是四下去寻冯绮夜。伊水之畔、关林庙前、白马古刹、永宁新寺,处处皆留下了高欢四顾怅然的身影,然而心上人儿却始终是芳踪杳然。高欢无奈之下,每每惟有望画兴叹,抑或是独捧锦帕,深嗅幽香、聊慰愁怀。每每此刻,俱恨不得快快一展抱负,待成就大业之时,找到心上人儿一圆绮梦便指日可望了。
又一日,高欢方从洛都驰归,途经建兴山道之时,猛可里风云突变,雷声隆隆、骤雨倾盆。高欢无处可避,仓促间抬首瞥得身侧斜坡之上枝叶掩映处好似有一洞穴,便径直打马奔了过去。
不料甫一入洞,却见洞中影影绰绰,似有一人席地而坐。自古荒郊野地先来便是主,高欢见丰识广焉有不知,于是忙翻身下马,便欲上前见礼。
欲知洞中人为谁,且容下回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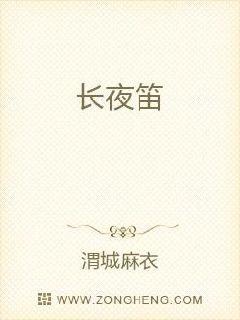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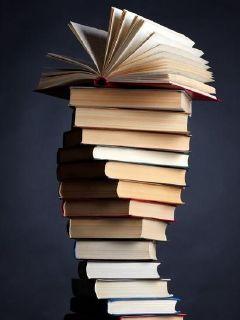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